夏晓虹:梁启超的历史意识
原标题:夏晓虹:梁启超的历史意识
在各种学问中,梁启超无疑对史学最执着,兴趣持久不变。晚年自我总结,也预言:“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许多宏大的着述计划,多属于史学题目,如《中国佛教史》、《中国学术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等。诸作虽无一完成,但从前二书的遗篇与后二书的全目,已可窥见梁氏均做了相当准备,且有了总体构架。至于文学史,梁启超也未留下一部完整着作,唯一一部以“史”命名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比较成形的也仅有“古歌谣及乐府”部分,其他“周秦时代之美文”、“汉魏时代之美文”及“唐宋时代之美文”,俱只成一二章。从内容的重复看,已可知其为未定稿。不过,这终究表明梁启超曾有心撰写文学史,尤其属意于诗歌史(或曰韵文史)。

天津梁启超故居
据《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21日张氏往访梁启超时,梁“言有论本朝诗学一稿,亦即可交稿”,此作当是因《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完成而引发。又《梁启超年谱长编》载三日前,梁氏有与胡适一信,谈及“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而《饮冰室合集》中未系年之《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恰有大段文字讨论白话诗,则梁氏信函与张氏日记所述,应同指一文,即梁启超为选编金和与黄遵宪二家诗所写之序。此书虽未编成,序文亦未写完,今日看到的,只有梁氏“向来对于诗学的意见”,而叙述“两先生所遭值的环境和他个人历史”及“对于他的诗略下批评”的史之部分,均付之阙如。然而,撰诗史之兴致确实从此提起,并以1922年最为集中,梁启超先后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含《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集考证》三目)等史论文结稿。嗣后,虽或暂时搁置,梁氏总会不断回到此大题目上来。1924年作《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次年成《桃花扇注》,临终前,尚力疾属草《辛稼轩先生年谱》。其欧游前后所拟着之《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史》,也都列有“文学篇”,欲分述文、诗、词、曲本、小说之发展。《陶渊明》一书《自序》更明言“夙有志于”“治文学史”,只因“所从鹜者众,病未能也”。
既然不可能集中精力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梁启超便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这也是他以为必不可少的步骤:
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此语可以视为梁氏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思路,即由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考察显示文学的历史变迁。就写作时间排序,《王荆公》应是最早一部包含文学史意识的评传。其中有两章专论“荆公之文学”,肯定其“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王安石之文虽称名“唐宋八大家”之中,然而梁氏视其为“学人之文”,“有以异于其它七家者”之“文人之文”。柳宗元、曾巩、苏洵、苏辙固不足与之相提并论,即使韩愈、欧阳修、苏轼三家文,王氏也以倔强肫挚而有一日之长。论及王安石之诗,梁氏断言其“实导西江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与其文气正是一脉相通。诸如此类,都从文学史着眼,而下确评。不过,此书宗旨原“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故特详于变革之新法,文学显然是叨陪末座,不以为主题,与1920年代以后论文学家之心事迥异,故下文不举为例证。
“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无疑是梁启超建构文学史的第一位工作。其所定入选标准共两条,即所谓“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在他眼中,显露鲜明个性比反映时代心理更为难得。因为有个性的作品须具备两个条件:“不共”和“真”。前者强调的是“作品完全脱离摹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后者看重的是“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以此二条衡量,够格的作家便极少了。“建安七子”的可见群体风格而难辨个人诗格,潘岳、陆机等人的过于注重辞藻而真情隐去太多,便都在摒去之列。遴选的结果:“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古代作家能彀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至于杜甫,“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诗中性灵尽现自不待言。词家中之偏爱辛弃疾,尝作《稼轩词系年考略》,汇校辛词,并录《稼轩集外词》48首题目,直至为其作年谱,也是因为“他是个爱国军人,满腔义愤,都拿词来发泄;所以那一种元气淋漓,前前后后的词家都赶不上”,与同为大家的苏轼、姜夔相比,“辛词自然格外真切”。曲词中之偏爱《桃花扇》,数十年如一日。晚清提倡文学改良时,撰《小说丛话》创小说批评新体裁,即是因1903年游美,“箧中挟《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馀条”,1925年夏,又为该曲作注,开卷有《着者略历及其他着作》一篇,看中的都是“《桃花扇》之老赞礼,云亭自谓也,处处点缀入场,寄无限感慨”,曲本中“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之《桃花扇》,冠绝前古矣”。上述诸作的性情之真切与显现之不共,在中国文学史中确是首屈一指,梁启超的眼光果然高超。而若以意境体格论,则金和与黄遵宪两家诗又被认作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以其筚路蓝缕的历史独创性,博得史家梁启超的极高赞誉,是以有手校《秋蟪吟馆诗钞》与《人境庐诗草》之举。
梁启超治文学史之法,与其所揣摩的《史记》立传深意同出一辙,“《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由此总结出:
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
这些不仅有“人格的伟大”而且有“关系的伟大”的“伟大人物”,“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也“可以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把那个时代或那种学术都归纳到他们身上来讲”。而其所推许的个性突出的作家,正能以标新立异、得风气之先而别开蹊径,导后人入新途。恰如梁氏构拟哲学史之分主系、闰系与旁系三条线索一样,选出各时期代表作家,等于确立主系,纲举目张,众多承流接响的作家作品,便可以其闰系资格,表现出各自在文学史上不同的地位。不过,此法与其说借鉴《史记》,不如说是得益于因西方评传体的引进而重新发现的《史记》。成书于1901年的《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序例》中即已言明:“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其史传作法之带有西方印记,已明白无疑。
以这种融会中西的眼光来观察,梁启超曾设想把中国文化分为“思想及其他学说”、“政治及其他事业”、“文学及其他艺术”三部分,“每部找几十个代表人,每人给他做一篇传”。其中关于文学的部分,便可视为其蓄志已久的中国文学史撰写章目,它由如下作家构成:
战国:屈原。
汉赋:司马相如。
三国五言诗:曹植,建安馀六子附。
六朝五言诗:陶潜,谢灵运附。
六朝骈文律诗:庾信,徐陵附。
唐诗:李白,杜甫,高适,王维附。
唐诗文:韩愈、柳宗元合。
唐新体诗:白居易。
晚唐近体诗:李商隐,温庭筠。
五代词:南唐后主。
北宋诗,文,词: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附。
北宋词:柳永,秦观,周邦彦。
北宋女文学家:李清照。
南宋词:辛弃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合。
元明清小说:施耐庵,曹雪芹。
王安石不在内,大约碍于分类体例,既已入“政治家”之列,此处便不录。孔尚任之缺席,则显然与梁氏以元、明为戏曲鼎盛期有关,其编排体例正显现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各时代代表性文学的习见。这也体现了梁氏“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的一贯原则。如诗史以唐朝为主系,“则以前以后,都可说明”,故“做诗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点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诗并不是没有派别,前七子,后七子,分门别户,竞争得很利害;但从大处着眼,值不得费多大的力量去看他们的异同”。而此目录所述虽是人物传记,归趣却在文学史,故首先作“《屈原传》以归纳上古文学”,将无主名之《诗经》放入其中论述。尽管梁启超对此名单是否妥当尚拿不准,真正动笔时“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这个目录”,但从中总能看出其心目中“某种文学到了最高潮”的代表作家基本分布状况及体裁的演进大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诸篇作家专论正是拟议中的中国文学史留下的片段。
第二步的工作是考辨时代背景与作者生平。梁启超向来服膺孟子的“知人论世”之说,并“以今语释”“论世”为“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梁氏认为:
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
既然梁氏以文学史之眼选中的作家,其作品当能映现时代心理,背景与人物自是融为一体,不可截然分开。将屈原与杜甫放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中来研究,以及描述晋宋交替之际的士风衰败、玄学盛行,以之为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及时代思潮的重要场景,都因非如此映衬,不能看清人物。而家世与履历的考辨,更为诠释作品必不可少。只是作为文学史家,梁启超不仅关心前因,也注意后果,力求“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他把历史比喻为一条环环相接、继续不断的长练,认为:“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史家的任务,便是把历史的每个环节寻找出来,按照来龙去脉的顺序连缀一起,再现历史演化的进程。在梁启超看来,这一进程显然具有受因果律支配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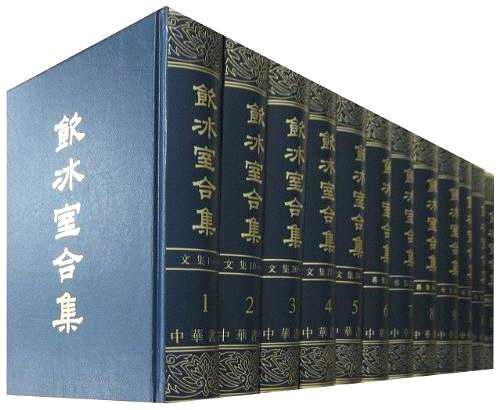
《饮冰室合集》
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当然是显现作家独特性格及思想情感的作品本身。梁氏如何从“实质”与“技术”两方面切入,前文已有论述,兹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文学史着述方法,在理论上存在着缺失。力图使历史有序化,过于重视因果律的作用,对于史学着作固然由于叙述方便而有可取处,却也容易导向忽视偶然性、变异性的误区。人类的精神活动本无法规范,何况梁氏也承认文学家往往特立独行,异于常人,性格“大与科学相反”,自然不能用自然科学中通行的因果律解释所有文学现象。在大思路上肯定梁启超“知人论世”说法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想指明其中隐伏的陷阱,无非是因为这一源远流长的着史法则,确乎在文学史界长期独领风骚,而阻碍了文学研究的深化。当然,这个责任不能由梁启超一人承担。
因果律之由结果返求原因,以环环相扣,已然是文学史结构的主要形式;而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入,更为解说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别一种理论范式。二者在强调必然性上获得一致。逆反于传统的“文学退化观”,近、现代学者有意无意漠视了“进化”语义中原有的“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的向下一面,更愿意将“进化”理解为“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文学无论体裁、技巧还是观念,也都相应有一从简单到复杂、从稚拙到成熟的演进过程。以“进化”一语概言之,便不可避免地染上包含其中的价值判断意味。梁启超也是风气中人,并且还是“进化论”的热心倡导者,对运用此学说于文学史研究,自然出力不小。其名言如: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日后胡适之着《白话文学史》,未尝不受此启发。不过,若以不断上进解中国文学史,原有许多扞格难通处。即以梁氏所述俗语文体之兴衰而言,自“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到六朝、唐代而中落,宋以后又出现“俗语文学大发达”,降至清朝又生顿挫,俗语文体并非渐进不衰。其实,承认文学有其不同于自然、社会的演化方式,在“进化论”大师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那里已经网开一面。梁启超曾征引其说:“宇宙万事,皆循进化之理,惟文学独不然,有时若与进化为反比例。”并称“其言颇含至理”,但这照样不能动摇其文学进化观。在概言“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的文化退化事实,以证斯宾塞言之有理后,他仍然要分辩:“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根据正是“进化论”的基本法则:“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则愈简单,愈高等者则愈复杂,此公例也。”按诸诗体,由四言渐进为五言,由五言渐进为七言,由七言渐进为长短句,由长短句渐进为曲辞,均呈现为愈趋复杂的走向。由于梁启超将曲本归入广义的诗,视曲本体裁于诸种诗体中“其复杂乃达于极点”,故盛赞“中国韵文,其后乎今日者,进化之运,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则吾必以曲本为巨擘矣”。不只体裁,在技巧方面,梁启超实际也首肯进化说。他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所言考证古人作品真伪与年代的两种方法,其“直觉的”一种便是建基于进化观念,相信“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为诗歌创作的大势所趋,才可以通过“和同时代确实的作品比较”而推断存疑之作的产生时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典范性考证,便是“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为这组作品在时间轴上定位的。
一般而言,日益完善可以作为文学史的通则来使用,否则无名氏作品的考证便无法进行。不过,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科学技术,作家的才能对作品的艺术水准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后必胜前并非铁律;何况,简单/复杂、古拙/精致未必可以落后/先进的价值评估论断之。即使单就形式、技巧而言,梁启超之说也有不尽然处。其实,梁氏对此并非毫无意识,起码在研讨中国诗歌的表情法时,便每以《诗经》为“绝唱”。在情感领域,他干脆承认:“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进而为了“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断案,得出“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的推论。不过,正如同他发现从元到清,中国戏曲“退化之程度,每下愈况”,却认定“诗乐合一”为历史进化的方向,俗语文体虽屡受挫折,文言向白话靠拢之趋势终不可逆转,在放长的时间段上,梁启超相信文学总体是在逐渐进步。
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律与进化思想,梁启超晚年有过重新检讨。1902年撰写《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时,梁氏即将“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确定为“新史学”之职志,二十年来从未改易。迨至1922年11、12月于南京讲学,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演讲,专门对年初出版的着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进行补充与修正,这一史学定义才被作为问题提出。文章将人类活动分为自然系与文化系两类,分别探讨了“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在两类活动中的不同表现。梁氏承认,由于他对“科学精神”的推崇,“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所以曲意维护史学以“求得其因果关系”为职责的说法,以致与“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之言前后矛盾;又因为“一治一乱”的循环论和他“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而厌恶此说。经过慎重思考,梁启超得出了新的结论:自然系的活动“受因果律支配”,具“非进化的性质”;文化系的活动反之,“不受因果律支配”,具“进化的性质”。只是,文化系的活动中,梁氏又分出文化种与文化果之别:
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
然则,研究“爱美的要求心及活动力”的文化种所产出之文化果“文艺美术品”,仍然可应用因果律了。这与他并不认可“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的简单排比,而将进化理解为“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的继长增高一样,在文学史范围内,他的观点前后并无大变化。
像治汉学出身的人一样,梁启超也有历史考据癖。借用他在《慧观》中的说法:
同一书也,考据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考据之材料;词章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词章之材料;好作灯谜酒令之人读之,所触者无一非灯谜酒令之材料;经世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经世之材料。
梁启超既认为“中国古代,史外无学”,故一切着述皆以史料视之。非只“六经皆史”,文学作品亦然,“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他在“‘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以及子虚乌有的小说中,不仅发现了“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进而以史家之“炯眼拔识之”,读出其中极珍贵的古代社会史资料。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在《山海经》中寻找“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以《水浒传》鲁智深醉打山门、《儒林外史》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范进,印证“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诸事实,都可谓别具只眼。小说之能够成为史料,是因为作家无论如何驰骋想象,“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从史学家的立场看,这确乎使“古今之书,无所逃匿”,无往而非史也,堪称得“善观”之妙。尽管梁氏浓厚的历史意识,使他在文学研究之外,赋予作品别一种功用价值,一如其要求文学能够改良群治、有益人生,却尚不至溺而不返,在其文学史研究论着中,文学眼光仍是主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诸文俱在,无须多言。
梁启超治学很信服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郑丈用牧书》)之言,故观点屡有修正,论述每求出新。做考证也是如此。考据本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梁氏于治文学史疑案中常用之。而其考辨所得,常常因异于成说,引起学界争议。其《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所引发的讨论与文学无关,可以不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提出“《老子》这部书的着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并举出六项根据以证其说,引起轩然大波,便关乎文本,与文学史相交涉。纯然属于文学范围的标新,如《陶渊明年谱》之推定陶潜“卒年仅五十六”,一反旧史旧谱之六十三岁说;《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怀疑《孔雀东南飞》“起自六朝”,与《玉台新咏》所载诗序“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的汉诗旧说相左,都曾成为聚讼热点。赞同前说者有梁氏弟子陆侃如,反对最力者为游国恩,其《陶潜年纪辨疑》逐一反驳了梁氏之八条举证,主张五十二岁说的古直也参与辩难;张大后说者除陆氏外,以张为骐论言最辩,驳诘一方的主将为胡适,黄节亦不以为然。陶潜卒年新说未成定论,而《孔雀东南飞》之年代梁启超当时说“别有考证”,而终于未见,稍后作《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时,已自放弃而加以更正,既破人蔽,又破己蔽,却都因善于发难,而导向研究的深入。对梁氏未必总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结论,应作如是观。
至于梁启超反对帝王史、倡导国民史,其主张也以摧陷廓清之力,于打破旧史观的同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使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进入研究者视野,并迅速上升为显学。其间的关联至为明显,尽管梁氏只有寥寥三两篇不怎么学术的小说论文,并未写过俗文学史题目的专论。这恰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映了梁启超文学研究的历史状况:其文学论着不必多,论述也容有疏阔可訾议处,而其“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势,便足以为他在学术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奠定不可回避的重镇地位。
(本文摘自夏晓虹着《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东方出版社,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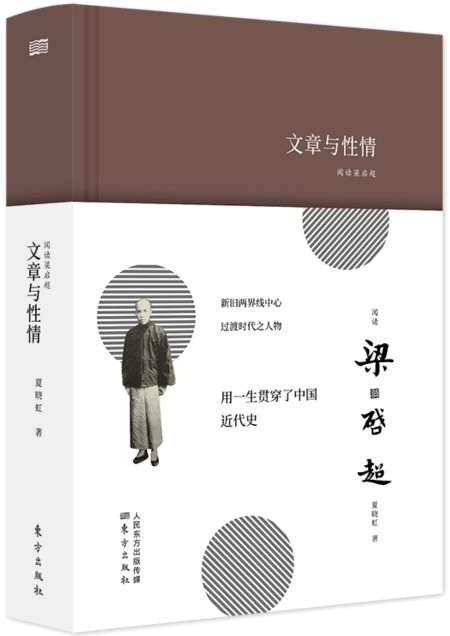
免责声明:
2.本网站刊载的各类文章、广告、访问者在本网站发表的观点,以链接形式推荐的其他网站内容,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供用户参考使用或为学习交流的方便(本网有权删除)。所提供的数据仅供参考,使用者务请核实,风险自负。
查看更多

 评论
评论

























